开卷有益
悦 读 会 Vol 5
勤于思而敏于行,
读书一直是国富人倡导的学习方式。
读书的态度和类型应当是多元化的,
并不局限于本职工作的领域。
今日点滴的积累,焉知不能在将来聚沙成塔。
“开卷有益”是国富的文化传统,
每一期都会有许多同事通过书评的形式分享好书。
读书使你我辽阔与丰厚,愿读书与我们长久为伴,
让这一天也不断流的潺潺小溪充实思想的河流。
![]()
No.4
April
2020
分享书籍: 《 诗词格律 》
王力 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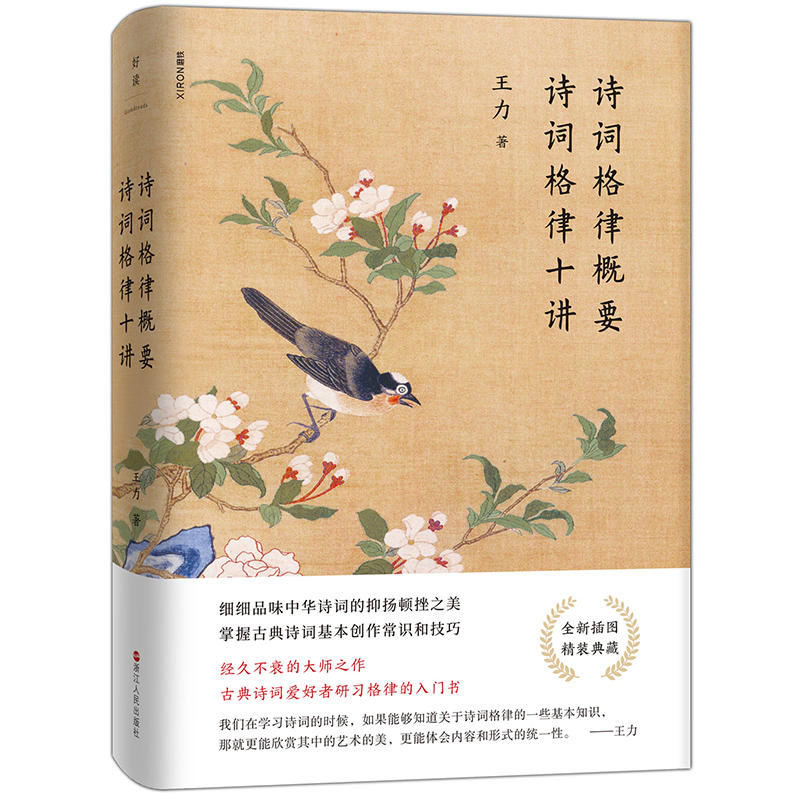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:作者的初衷在于将诗词格律作为一种基本知识来告诉读者,故而简明扼要、深入浅出、便于学习是其最大的特点。全书共四章:第一章介绍诗词格律的一些基本概念,包括韵、四声、平仄、对仗等;第二章分别讲解律诗、绝句、古体诗的诗律;第三章讲词律,分为词的种类、词谱以及词韵、词的平仄与对仗三小节;第四章讲诗词的节奏及其语法特点。
作者简介:王力(1900―1986)语言学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、散文家、诗人,中国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,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,师从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陈寅恪等。后留学法国,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。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北京大学等校教授。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世纪,在汉语语法学、音韵学、词汇学、汉语史、语言学史等方面影响深远。
书评作者 | 褚爷
诗词是每一个中国人自小就接触的,大概到高三到达储备量的巅峰,此后便直线下滑。如此算来,就当我们7岁时学会人生中第一首诗,到19岁高考结束,我们有计划地学习诗的时间也有12年左右。
但可惜的是,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对于诗的理解仅停留在背诵和了解基本意义,可能在工作之后连这两点都渐行渐远了。
语言学泰山北斗王力的《诗词格律》在这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发,借助读书会,愿与各位朋友分享一二。
有许多人所了解的诗的韵律,仍然认为只需每句最后一个字的韵母相同,听上去朗朗上口,即为“押韵”,如此这般,那作诗也太简单了,殊不知,诗中的技术性格律问题,古往今来,许多人穷尽一生都未能完全掌握。
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有很多种,今天既然讲的是诗的格律和艺术性问题,我们就遵照格律与否,将古代诗歌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。
看到这,读者想必已经心生疑窦,新文化运动里的胡适,朦胧诗派的北岛、顾城,他们写的不是近体诗吗,那可都是白话文呀,哪有格律可言?
这里就引出了诗的分类中的一个误区:近体诗是以唐人所处的时代为区分的,唐人将早于唐朝的诗称为古体诗,格律诗在唐朝逐渐发展成熟,是为近体诗,这两个词都是沿用千年的专用名词。
日常生活中,我们将所有的古代诗歌称为“古诗”是不对的。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,应称为”新诗”或“现代诗”较为妥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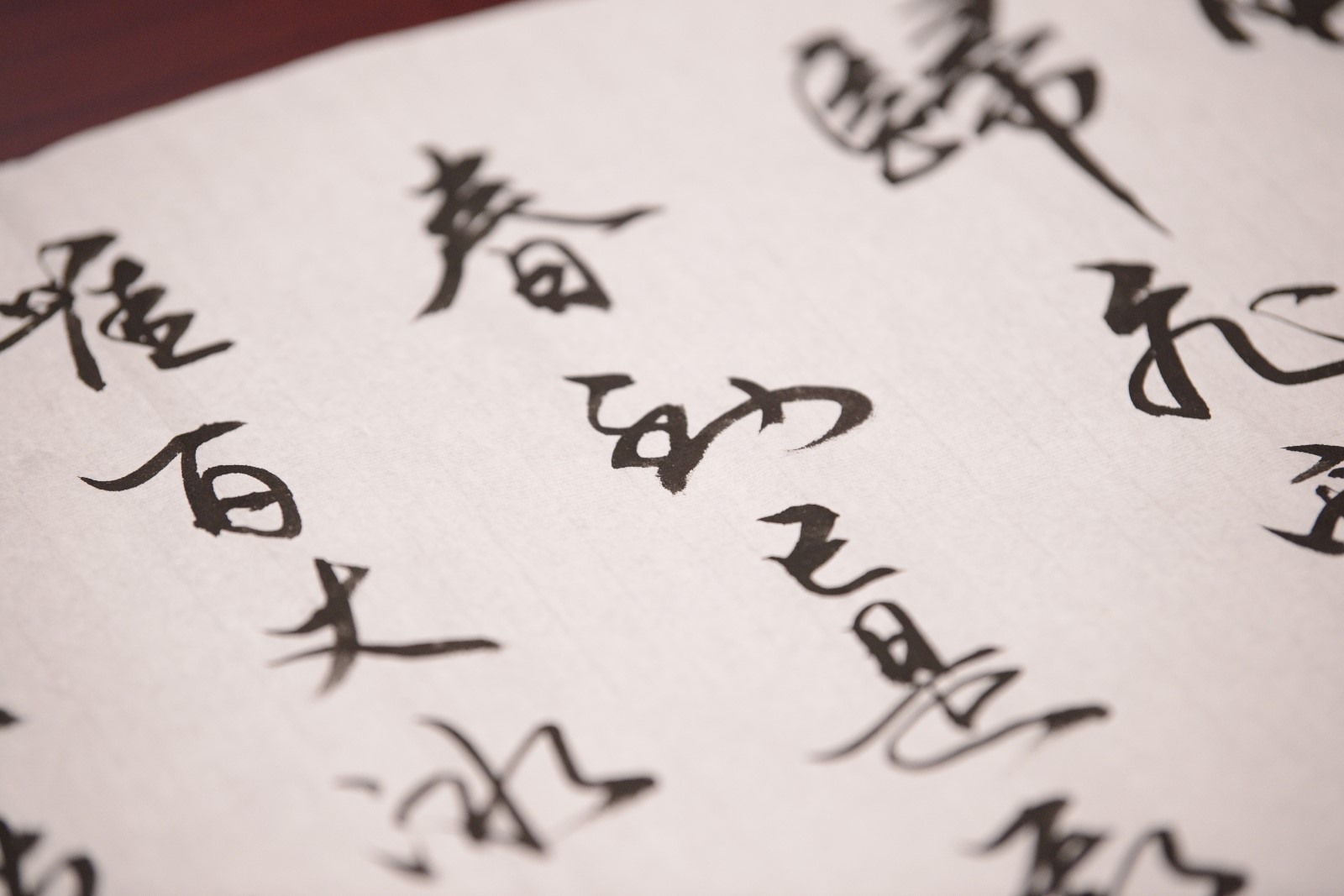
Photo by Yifeng Lu on Unsplash
我们读过的许多唐以前的诗歌,比如曹操的“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”《龟虽寿》;他儿子曹植的“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《七步诗》。
这些诗,在平仄、对偶、用韵等方面还没有自觉性的发展到唐朝格律诗高度成熟的程度,不受格律束缚,只需大体上押韵即可,这一类诗叫做古体诗。我们知道的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汉乐府诗等都可以归为古体诗。自唐以降,大部分的诗作都属于格律诗了,当然也有诗人为追求高古,继续写作古体诗的,比如李白的古风堪称极品。
那么,究竟什么是格律诗?
我们先来讲平仄。
平仄 ▉
平声可分为阴平和阳平,对应的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第一声和第二声;仄声对应的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第三声和第四声,以及最要命的入声。
到底什么是入声字呢?
如今的北方话当中已经完全没有入声字了,西北、西南(云贵川)讲的也是和北方话差不多的官话语系,自然也没有入声字。
只有苏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江西和北方的山西等地较为完整的保留了入声字,如果你来自于这些地方,你可以使用家乡方言尝试读一下“白”、“出”、“石“、“热”这几个字,简单来讲,这几个字都是“发音短促急收藏”,一个短短的爆破音节,马上声音就收回去了。这样的字,就是入声字。

Photo by Toa cullen zh on Unsplash
对于今天的北方人来说,要弄懂入声字,唯有死记硬背。因为入声字在今天的普通话中,分布在一声、二声、三声、四声的都有,这给我们学习格律诗带来了很大困难。先来看最简单的五言绝句:
登鹳雀楼 唐·王之涣
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
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
按照普通话发音,这首诗四句话的平仄为:
平仄平平仄,平平仄仄平。
仄平平仄仄,仄仄平平平。
这么看,《登鹳雀楼》全诗平仄错乱,相邻两句的平仄完全没有对应,毫无音韵之美,是王之涣不懂平仄吗?当然不是,问题还是出在了入声字,诗中加了着重号的字均为入声字,归为仄。这样全诗的平仄就变成了:
仄仄平平仄,平平仄仄平。
仄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
(五绝第三句首字可平可仄,此处用仄不算出律)
有人说,“黄河入海流”改成“大河入海流”不行吗?
如果“黄”改成“大”,平声就成了仄声,就出律了,此乃格律诗禁忌,当然不行。这首诗短短20字,平仄工整,描写了大气磅礴的景致,还蕴含着昂扬向上的人生体悟,不失为一首五绝佳品。
难怪郭沫若先生说,诗就要是要用最简洁的语言,写出最丰富的内容。
除了《登鹳雀楼》这种平仄调式外,五绝还有“平平平仄仄,仄仄仄平平。仄仄平平仄,平平仄仄平”等调式,七绝的变化就更多,在此不赘述了。

Photo by Yue Iris on Unsplash
绝句毕竟只有四句话,且对于对偶等要求不如律诗严格,而律诗有八句话,无形中平仄难度又上了一层,我们看一首杜甫的五律—《春夜喜雨》。
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
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
野径云俱黑,江船火独明。
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。
同样的,按照普通话发音,这首五律处处出律,但是即使按照加了着重号的字为入声字处理后,仍然有个别字的平仄对不上。
如颈联“俱”在此处应为平声,但普通话发音为第四声,“黑”此处应为仄声,但普通话为第一声。尾联“看”应为平声,但普通话发第四声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这里就牵涉到一字两读的问题,有点接近现在的多音字。
古代诗歌中,许多常见字都有与今天的读音不同,在表达不同意思,不同词性时声调也不同。如这首诗里,“俱(jū)”“黑(hè)”、“看(kān)”才是正解。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,这几个两读字在格律诗里都采用这种发音,而非普通话发音。
还是拿这几个字举例,毛泽东《沁园春▪雪》中“俱(jū)往矣,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。”如果按照第四声去读,则不符合沁园春词牌的平仄了,毛泽东无愧为诗词大家。
李商隐《无题▪相见时难别亦难》中“此去蓬山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(kān)”才符合格律。另外较为常见的两读字还有很多,都是格律诗中必须掌握的。比如“教”,古诗词中基本读第一声,如“不教胡马度阴山”、“问世间,情为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等。

Photo by cullen zh on Unsplash
七言律诗中的平仄调式更多,且有孤平、失粘、失对等问题,古人认为是作诗时的洪水猛兽,在此按下不表。
相信各位读者看完对平仄的基本介绍后,即便仅仅是简单的五绝和五律平仄,也已经感受到了格律诗巨大的创作难度,别急还有更难的,那就是律诗的韵。
韵 ▉
写律诗,是要严格按照韵书押韵的,什么是韵呢,简单地说就是每联最后一个字的韵母,押韵就是每联最后一个字要出自同一道韵。
比如李白的《春晓》,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,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。按照普通话定义,它押的是ao韵,那是不是搞懂汉语拼音就会押韵了呢,哈哈哪有这么简单。
诗有106道韵,称为平水韵,是以江浙语音为基础的,即使到了词当中有所简化,仍然有57道韵(词被称为诗余,从地位上先天的就低于诗),即便是最简单的戏曲,仍有13道辙。我以上平声15韵简单举例说明:
一东(ong) 二冬(ong) 三江(ang) 四支(i) 五微(ei)
六鱼(u) 七虞(u) 八齐(i) 九佳(a) 十灰(ui)
十一真(en) 十二文(en) 十三元(an) 十四寒(an) 十五删(an)
东、冬两字在普通话中发音完全一样,而且在今天的吴越方言、闽南语、客家话、广府话、潮汕话中发音也一样,但在韵书上却分属两个韵部,如果你在诗中韵脚上出现了分别属于东部和冬部的字,那就是出韵。
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东和冬属于不同韵部的问题,语言学家至今似乎仍然没有定论,只能推测在上古汉语时代,东和冬的发音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同样的十四寒、十五删发音也很接近,每个韵部中又有上百个字,极易混淆。
《红楼梦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,林黛玉叫香菱写一首咏月的律诗,指定用寒韵,探春在一旁隔窗说笑:“菱姑娘,你闲闲吧。”香菱怔怔答道:“闲字是十五删的,错了韵了”,可见近体诗用韵之严格。

Photo by Yue Iris on Unsplash
有人看了几部穿越古装片,就认为自己回到古代可以凭借背好的诗混个大诗人的名号,殊不知古时文人都是觥筹交错之间,即兴按韵脚现场作诗,到时候现代人可就原形毕露了。
要将平仄和韵弄懂,算是刚刚过了格律诗技术上的关卡,现如今仍然有不少勤奋刻苦之人,在几年之中可吃透平仄用韵,可以写出技术性上没大毛病的诗,但是必须在一旁查阅韵书,我想1300年多前,杜子美登上泰山后,难道要掏出一本韵书才能写出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?
对仗、合掌 ▉
平仄和韵都是格律诗中技术性的问题,上到诗词的艺术性,那又是另一番维度了。对仗既是技术要求的一部分,也是体现诗人艺术创造力的一个方面。
诗词中的对偶,叫做对仗。古代的仪仗队是两两相对的,这是“对仗”的来历。对仗的一般规则,是词性相对,名词对名词,动词对动词、副词对副词,各种词性下又会有细分,颜色对颜色,天文对天文,但为保艺术性亦可宽对,在确保词性一致的前提下,天文对地理也是可以的,所以对仗亦有很高难度。
绝句只有四句,不要求一定对仗,但律诗的颈联、颔联(第三四五六句),一定要对仗,尾联因为要总结主题,升华情感,可对可不对。以杜子美的《登高》为例:
登高 唐·杜甫
风急天高猿啸哀, 渚清沙白鸟飞回。
无边落木萧萧下, 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。
艰难苦恨繁霜鬓, 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全诗平仄,韵律当然完全没有问题,颔联“无边”对“不尽”,“落木”对“长江”,“萧萧下”对“滚滚来”,对仗精严,让人一听便身临其境,被诗人带入了秋天萧条浑凉的意境中,颈联也是环环相扣。即使是不强求对仗的尾联,杜甫也做到了基本对仗,但若仅仅是格律工整,此诗还不足以流传千古。

Photo by Sonia Benhamou on Unsplash
杜甫作此诗时,安史之乱已结束四年,杜甫也因战乱在各地漂泊了十年,国家仍然满目疮痍,自己也走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,因病戒酒,连借酒消愁也无可能了,登上高台,望着眼前景色,写下了这首沉郁顿挫,高浑博大的“古今七律第一”。
对仗当中,完全同义的词相对,似工而实拙。一联中,出句与对句完全同义(或基本同义),叫做合掌,是诗家大忌。如“马上逢寒食,途中属暮春。”纪昀评论说:“途中、马上,寒食、暮春未免合掌。”的确,这两对词组,意思是相近或相同的,等于一句话说了两遍,有合掌之嫌,诗中应尽量避免。
流水对是对仗中一种高水平的表现形式,如杜甫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”、“即从巴峡穿巫峡,便下襄阳向洛阳”,不仅天衣无缝,还在对仗之中叙述了事情经过,诗圣功力之深厚,令人惊叹。
才思 ▉
一首诗在满足了所有的技术要素后,若是没有“诗味”,我觉得仍然很难称其为诗。必须承认,写诗是要才思的。
遗憾的是,才思可能真的无法靠刻苦获得,历史上许多下了功夫将平仄韵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人,最终都败在了才思上。“一寸光阴一寸金,寸金难买寸光阴”,算诗吗,当然算是,但是这平铺直叙的大道理,全然没有诗的意境。
但如果看李商隐的“春心莫共花争发,一寸相思一寸灰”,立马便能体悟到诗人相思到极点后的悲痛。向往美好爱情的心愿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,因为寸寸相思都化成了灰烬。诗人由香销成灰联想出“一寸相思一寸灰”的奇句,化抽象为具象,用强烈对比的方式显示了美好事物之毁灭,使这首诗具有一种动人心弦的悲剧美。
再比如唐朝李绅的《悯农》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,我虽没有认真考证过,但我严重怀疑《悯农》的流行,更多的是因为建国之后物质资源的匮乏,作为教育标语存在。它的教育意义远大于它的艺术意义,这样的诗应是入不了古人法眼的,难怪我们今天只读到过李绅这一首诗。
如若没有了格律的束缚,我们写古风诗,乐府诗是不是就能和古人正面刚了呢?别忘了在古体诗界还有李白这一尊几乎无法逾越的大神。
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唐▪李白
弃我去者,昨日之日不可留;
乱我心者,今日之日多烦忧。
长风万里送秋雁,对此可以酣高楼。
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。
俱怀逸兴壮思飞,欲上青天揽明月。
抽刀断水水更流,举杯销愁愁更愁。
人生在世不称意,明朝散发弄扁舟。
到底是怎样奇诡的想象力,才能将愁绪比作利刃都无法斩断的流水?又是怎样坚定的理想,能支撑诗人一再受挫后,只需泛舟湖上,就能潇洒再来一回呢?
我仿佛能看见李白一人着一身青色长衫,躺在一只小小的木船上,荡漾在桃花潭中,不问世事。换做是被抖音、微博荼毒的我们,大抵只能喊出一句“卧槽,我好南”吧。

Photo by Caroline_S on Unsplash
结语 ▉
格律诗因为极其严格的规范和极高的审美要求,是汉字意美、音美、形美的终极体现。
近代以来,有不少人望而却步,或是提出要简化格律诗。我想,人们若是在平地奔跑,则平平无奇,但如果能在钢丝上起舞,那才值得喝彩。
平仄韵律从未成为先贤们的枷锁,反而他们在其中游刃有余,艺术上只有具备了一定的门槛,才会让人感觉倍有嚼劲。
我从未怀疑过新文化运动的意义,它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愚昧,迎来光明。我也不会幼稚到去否定矫枉过正的弊病,一场社会运动,一次政治浩劫,为了彻底肃清一种势力,当然是要矫枉过正的。
但是在100年后的今天,义务教育即将达到12年的时候,面对社会媒体及党政刊物中诸多名不副实的《七律XXX》《五律XXX》,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反思,这100年间我们到底丢掉了什么。
当一切都无可挽回的走向庸俗的时候,我很庆幸,古典的堡垒仍然高高在上,她守卫着我们内心深处最后一丝圣洁。
···生命有限,让读书使你我辽阔···

版权声明及风险提示
本官网刊载内容仅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,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和销售要约。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,未经版权方许可,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、复制、刊登、发表或引用。